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摘要:“Auslegung”属于诠释学的核心概念,汉语学界有“解释”和“阐释”不同译名。从现代诠释学创立及至当代发展,这一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演变,形成“客观义”和“延伸义”两种截然不同的旨趣。当代方法论诠释学的集大成者贝蒂,致力于廓清“Auslegung”概念的复杂性,重塑其内涵和外延,捍卫解释的客观性要求,使之区别于“思辨的赋义”(spekulative Deutung)。深入考察这一概念的演历、当代方法论诠释学的重塑,及其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之争,对于处理诠释学发展中的种种分歧、汉语学界的不同理解以及译名争议,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解释/阐释;赋义;含义的同一性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22年第12期。 目次 一、从“解释”到“阐释”:“Auslegung”的涵义嬗变及困境 二、客观性重塑:区分“解释”和“赋义” 三、“解释”能否通达含义的同一性 余论:“Auslegung”的汉译问题 “Auslegung”是诠释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汉语学界有“解释”和“阐释”不同译名,从现代诠释学创立及至当代发展,这一概念始终具有不可回避的重要性,近年来又成为探讨的热点。其中包含两种截然不同的旨趣,一种侧重“客观义”,即对文本、作者原义/原意的考证、重构和展开;另一种着眼于“延伸义”,即理解者对文本或自身存在意义的开显、阐发以及创造。对“Auslegung”的理解成为诠释学流派分野的重要标识,无论是方法论诠释学和本体论诠释学赋予它的不同内涵,还是汉语学界关于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译名分歧,都反映了不同诠释学理念之间的冲突张力。 诠释学经历本体论变革之后,方法论诠释学再度崛起,当代方法论诠释学的集大成者贝蒂(E. Betti),致力于廓清“Auslegung”概念的复杂性,对其内涵和外延予以重塑,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在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交锋中,贝蒂通过把这一概念与“赋义”(Deutung)、“意义赋予”(Sinngebung)区别开来,重申解释的客观性要求;赫施(E. D. Hirsch)则通过区分含义(meaning)和意蕴(significance),重申解释的有效性要求。厘清“Auslegung”概念的涵义嬗变及困境、当代方法论诠释学对这一概念的重塑,及其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之间的争论,对于深入思考诠释学发展中的种种分歧、汉语学界的不同理解包括相关译名的争议,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从“解释”到“阐释”: “Auslegung”的涵义嬗变及困境 “Auslegung”的诠释学含义以日常语义为基础,在日常德语中该名词意为解释、阐释、注释,规划、布局;相应的动词“auslegen”,字面义为打开、陈列、铺放,引申为解释、注释,设计、规划。这些含义相近相通,不同的中文译法往往可以互换。但作为诠释学的术语,不能停留于日常语义,而需要进一步辨明其哲学上的涵义及演变。 浪漫派诠释学是现代诠释学的第一个形态,最早厘定“Auslegung/auslegen”的内涵和外延。施莱尔马赫频繁使用这一概念,也经常将它与拉丁语源的“Interpretation/interpretieren”作为同义概念交替使用,“其实无论是施莱尔马赫、狄尔泰,还是伽达默尔对‘Auslegung’和‘Interpretation’都没有做严格的区分”,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著作中找到多处文本依据。浪漫派诠释学明确提出理解的客观性要求,并制定了相应的方法论规则,将“Auslegung/auslegen”“Interpretation/interpretieren”的概念内涵确立为以重构文本和作者原义/原意为目标的解释,鉴于此,这里我们姑且译为“解释”(译名探讨见本文余论)。施莱尔马赫在1805−1809年的《诠释学箴言》中强调,“解释(Interpretiren)过程中的要事在于,必须能够走出自己的意念(Gesinnung),进入到作者的意念之中”,排除理解者的偏见,避免随意的阐发,以便趋近文本、作者思想的原貌。施莱尔马赫要求区分“auslegen”和“einlegen”,尽管他未给出详细阐述,但这一提示对于我们理解其诠释学用意非常重要。这两个词词干相同,前缀不同,一个是“解开”“释出”(aus-legen),另一个是“置入”“嵌入”(ein-legen),前者旨在把原有的含义释放出来,后者则带有添枝加叶地发挥之义。诠释学研究的是“auslegen”,而不是“einlegen”,其核心要义就在于客观地呈现文本和作者原来的意思。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文本原义和作者原意并非总是等同,以致需要使两方面互相印证,才能实现更好的理解。施莱尔马赫指出,理解包含对语言表达的理解,也包含对言说者/作者及其思想的理解,“由于这种双重的理解,解释(das Auslegen)是一门技艺(Kunst)”,其“外延”包括语法解释(grammatische Auslegung/Interpretation)和心理学解释(psychologische Auslegung/Interpretation),二者构成解释的两大方法,分别基于语言的共性和个性。语法解释的任务是从含义的统一性和确定性方面来理解语言表达,心理学解释的任务则是理解作品的思想和作者的意图、个性。广义的心理学解释又分为纯粹的心理学解释(rein psychologische Auslegung)和技术解释(technische Auslegung),前者侧重对作者思想进程的动态描述,后者侧重刻画作品创作的风格形式。施莱尔马赫赋予语法解释和心理学−技术解释同等重要的地位,使二者相互补充,语言表达越具有客观确定性,就越需要语法解释,反之,越具有个性化的主观特征,则越需要心理学解释。解释的目标始终是原义/原意,甚至是“比作者理解得更好”的原义/原意,澄清作者本人未曾意识到、却潜在地包含于其意图和作品之中的思想。 狄尔泰延续并发展了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传统,《诠释学的起源》(1900年)一文对“理解”和“解释”进行如下界定:“从外在感官给予的符号去认识内在之物的过程,我们称之为理解”,“这种对持久固定的生命表现(Lebensäußerungen)的合乎技艺的理解,我们称之为解释(Auslegung)或阐释(Interpretation)”。显然,“Auslegung”和“Interpretation”被狄尔泰视为近义或同义的概念,综合考虑其术语内涵和词源学依据,我们分别译为“解释”和“阐释”。首先,狄尔泰的“Auslegung”和“Interpretation”概念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施莱尔马赫的“客观义”取向,具有“解释”的内涵,但句中“Auslegung”和“Interpretation”是同位语,若都译为“解释”,则译名重复。其次,狄尔泰的诠释学搭建了方法论诠释学向本体论诠释学过渡的桥梁,他赋予“Auslegung”和“Interpretation”的涵义也具有过渡性质,从“解释”向“阐释”、从“客观义”向“延伸义”过渡,或言之,兼有“解释”和“阐释”双重维度。在狄尔泰这里,理解的历史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合乎技艺的理解即解释,意味着解释主体进入生命−历史的关联中,通过部分与整体的诠释学循环获得对他人生命表现、精神客观化物的理解,理解和解释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具有历史性。狄尔泰固然孜孜不倦地追寻客观解释,同时又超越了仅以正确理解为目标的诠释学技艺,对理解的条件进行了自觉反思,解释过程中的效果关联(Wirkungszusammenhang)、历史因素凸显出来,突破对个别具体文本的客观“解释”,拓展到对理解者自身以及作为效果关联的整个精神世界、历史世界和生命洪流的“阐释”,表现为无限的意义生成过程。最后,相较于“Auslegung”,将“Interpretation”译为“阐释”符合词源学含义,更能凸显其活动主体的中介性与能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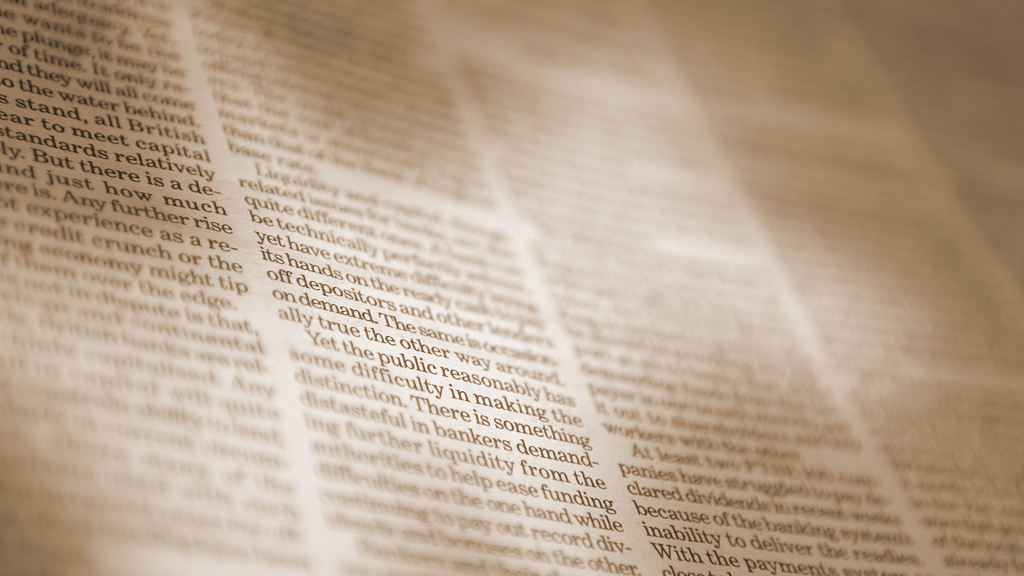 正是沿着“阐释”的道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实现了诠释学的本体论变革。《存在与时间》(1927年)确立了“理解”的本体论地位,理解成为此在(Dasein)的存在方式,“Auslegung”属于“此”(Da)的生存论环节,乃是作为此在的生存论展开和存在意义的建构。“Auslegung”的内涵经由狄尔泰到海德格尔这里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即从方法论意义转向本体论意义,它不再是客观解释之义,而是更加侧重于阐释,我们姑且按其内涵译为“阐释”。海德格尔的阐释概念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1)从理解与阐释的关系来看,一如“此在”是“去存在”(zu sein),理解就是向着可能性存在、进行筹划活动的能在(Seinkönnen);理解造就自身的活动即是阐释(Auslegung)。“在阐释中,理解把它所理解到的东西以理解的方式(verstehend)据为己有。理解在阐释中并不成为别的东西,而是成为它自身。在生存论上,阐释基于理解,而理解并非通过阐释而产生。阐释并不是要对被理解的东西进行认识,而是把理解中所筹划的可能性加以修整(Ausarbeitung)。”海德格尔将理解视为更加基础的概念,阐释植根于其中,同时强调这种阐释并非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对理解活动及其可能性的“修整”。理解着的此在向未来敞开,只有通过此在的展开(Erschlossenheit)才能达到源始的真理,阐释在此过程中发挥揭蔽的作用。(2)从阐释的结构来看,它具有“作为”(als)结构,即“把……作为……来阐释”,这种“作为”揭示了源始的、与上手之物打交道的关系,阐释不是将某种含义以“贴标签”的形式附加在现成之物上,所谓的现成之物本就处于世界理解的因缘关系(Bewandtnis)中,“这种因缘关系通过阐释被揭示出来”。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严格来说理解、阐释的并不是意义,而是存在者的存在,意义只是存在之可理解性的栖息之所。(3)从阐释的条件来看,它奠基于前拥有、前视见和前把握之中,这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诠释学循环。海德格尔一方面指出这一循环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要求警惕阐释的随意性,以现象学的“事情本身”加以约束。“关键不是摆脱循环,而是按正确的方式进入循环”,“阐释认识到,其首要的、持续的和最终的任务始终在于,不让前拥有、前视见和前把握每每以偶发奇想和大众之见的方式呈现,而是从事情本身出发来修整前拥有、前视见和前把握,以确保课题的科学性”。 到了伽达默尔这里,理解、“Auslegung”和应用(Anwendung)的绝对界限被打破,三者互相渗透。“Auslegung”不是跟随在理解之后的附加物,而是理解过程本身的展开,其中始终包含着应用,是过去与当下的中介活动;它不是原样地复制原义/原意,而是被理解之事与理解者自身的诠释学处境之间的视域融合,不是对现成意义的“发现”,而是意义在当下的生成与创造。伽达默尔的“Auslegung”概念侧重的显然是“阐释”,这一点从《真理与方法》(1960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文本与阐释》(Text und Interpretation, 1983)一文则较多地使用了“Interpretation”,如前所述,伽达默尔没有对这两个概念做出严格区分。何卫平先生指出二者在伽达默尔那里的细微差异在于,“Auslegung”突出的是海德格尔现象学意义上的解开、释放,而“Interpretation”突出的是翻译和转化的意思。无论如何,哲学诠释学不再致力于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客观解释,其“Auslegung”“Interpretation”概念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阐释,即多元意义在理解过程中的生成、阐发与创造。 从以上论述可知,“Auslegung”在诠释学发展史上形成了截然不同以至相互对立的双重含义:以客观义为中心的“解释”和以延伸义为中心的“阐释”。到了伽达默尔这里,封闭、固定的作者原意和文本原义不再可能,客观义被解构了,浪漫派诠释学的“解释”目标化为“阐释”的效果历史。本体论诠释学给方法论诠释学造成了巨大冲击,导致客观义失落,“Auslegung”概念陷入困境,客观解释的可能性面临挑战。当代诠释学家贝蒂意识到这种危机,对哲学诠释学展开批判,主张回到方法论诠释学的“解释”立场,将正确理解、客观理解作为诠释学的首要任务,并通过区分“Auslegung”和“Deutung”以捍卫解释的客观性。 二、客观性重塑:区分“解释”和“赋义” 贝蒂并不认为本体论诠释学能够取代方法论诠释学,诠释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维度不容忽视,正确解释文本、追寻客观含义依然必要,他对伽达默尔的批评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一点上,“我只想表明作为伽达默尔理论结果的客观性失落,不能由意识他自己历史性的主体所抵消;另外,提出的区分真假前见的尺度……依赖于自我欺骗,也就是说,它并不为理解的正确性提供一种可靠的标准”。在贝蒂看来,诠释学是关于正确解释的理论,应当成为精神科学的一般方法论,他的代表作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从这些论著可知,“贝蒂诠释学取法方法论,并在其标题上明确用Allgemeine Auslegungslehre(一般解释理论)取代Hermeneutik,或者以allgemeine Methodik(一般方法论)界定Hermeneutik,都意在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根本立场”。那么,如何回归诠释学方法论的客观性、正确性要求?澄清并重塑“Auslegung”概念至关重要,贝蒂对这一概念进行严格限定,重建其“客观解释”之义,使之区别于“思辨的/玄想的赋义”(spekulative Deutung)。  以客观义为目标的“Auslegung”,正如动词“auslegen”所刻画的那样,把某个东西打开、陈列、呈现出来,所展示的无非是本就存在的,对于文本而言就是“解释”,亦即把文本/作者固有的原义/原意如其所是地解开、释放出来,而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不能把解释者的“主观”见解随意地强加于作者或塞入文本之中,否则就是一种“强制阐释”。贝蒂将施莱尔马赫提及但未详细阐明的“auslegen”和“einlegen”之区别,追溯到解经学的著名原则:Sensus non est inferendus sed efferendus(意义不能[从外部]输入,而必须[从经文中]带出)。他援引这一原则意在表明,文本解释过程中要避免从外部“输入”文本本身所不具有的意义,只有从文本中“带出”的意义才是其固有意义的展现。正确的解释就在于使文本固有的意义呈现出来,它是可检验的,遵循客观性的标准。贝蒂强调,即使所有的认识和理解都难免带有某种视角特征,但“人们能够并且必须区分真实的、真正的解释(dem wahren und eigentlichen Auslegen)和玄想的赋义(dem spekulativen Deuten)……后者是从某种设定的世界观立场出发而进行的意义赋予(Sinngeben),旨在使经验事实与这种世界观协调一致,并使之嵌入世界观体系的整体关联之中”。只有“解释”才是理解文本的客观有效形式,“赋义”则是一种基于主体世界观立场的玄想的构造(spekulative Konstruktion)。将“解释”与“赋义”“意义赋予”区别开来,是贝蒂廓清“Auslegung”概念的重要举措。 仅仅宣称客观解释的主张还不够,需要从学理上说明,客观解释何以可能。贝蒂看到解释过程的“二律背反”,这是由诠释学的对象性质决定的。诠释学的对象被称为“精神的客观化物”“富有意义的形式”,包含物理层次的知觉载体和精神层面的意义内容,后者才是诠释学所涉及的真正内容,“凡在某种由他人精神而来的东西接近我们时,就有一种召唤我们理解能力的呼吁,希望它们得以被展示”。理解和解释就意味着将对象的物质符号转换成思想和意义,这种转换不是机械的,而是主动的、能思维的解释者对创造过程的倒转,“解释者必须通过在他内在自我内重新思考富有意义形式而从相反的方向经历原来的创造过程”,是一种重新认识和重新构造。理解和解释其实就是精神与精神的沟通,是主观性与主观性的转换,以理解者的精神、主观性去构造作者的精神、主观性。其中的“二律背反”在于,“一方面是那种不能与理解自发性相分离的主观因素,另一方面是作为要达到的意义它在性的客观性”,这种张力构成了解释过程的辩证法,包含解释者、有待被理解的精神和富有意义的形式三个要素,是三者的辩证统一。 贝蒂诠释学致力于解决解释的客观性和正确性问题,他虽然承认解释者的主观性必须参与到解释过程之中,情境主义的意义变迁在所难免,但坚持认为必须将解释和意义赋予、赋义区别开来,通过诠释学原则、方法论的控制来捍卫精神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为此,他提出诠释学的四条方法论原则:诠释学的对象自主性原则,意义融贯原则/整体性原则,理解的现实性原则,以及诠释学的意义符合原则。前两条原则涉及解释的对象,后两条原则涉及解释者主体。贝蒂还综合以往方法论诠释学的成果对解释的“外延”进行划分,构造了一个庞大的解释类型学系统,如语文学的解释、历史的解释、技术的解释、复现的解释(翻译)、戏剧的解释、音乐的解释、规范的解释(法律解释)、神学解释和心理学解释,以此作为解释客观性的保障。 对象的自主性(Autonomie/Eigenständigkeit)是解释的内在性原则,“解释”与“赋义”的区分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富有意义的形式必须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并且必须按照它们自身的发展逻辑,它们所具有的联系,并在它们的必然性、融贯性和结论性里被理解;它们应当相对于原来意向里所具有的标准被判断:这个原来的意向就是被创造的形式应当符合的意向即从作者的观点和他在创造过程中的构造冲动来看的意向。由此推知,它们一定不能根据它们迎合于似乎与解释者相关的任何其他外在目的来被判断。”对象的自主性是理解之客观性的根基和内在标准,解释活动不应迎合解释者的外在目的,而是要使解释符合作者和文本的原有意图。当然,贝蒂的诠释学并不是素朴的客观主义立场,其认识论是后康德式的,他指出,“有些历史学家试图让自己抛弃他们的主观性是完全无意义的”,“我们心灵所获得的任何东西都进入了我们自己已经具有的我们表象和概念的整个结构之中”。客观解释既不是被动的镜像反映,也不是心理主义的回溯,而是理性的认知论,在解释主体的积极参与中趋近客观的理解,理解要符合被理解的对象,“这包含一种在道德和理论上均是反省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等同于无自我性和谦逊的自我消除”,以无偏见的态度从事解释,解释者的自发性(Spontaneität)固然是必要的,“但不能从外部蔓生而盖过被解释的对象,并且强加于被解释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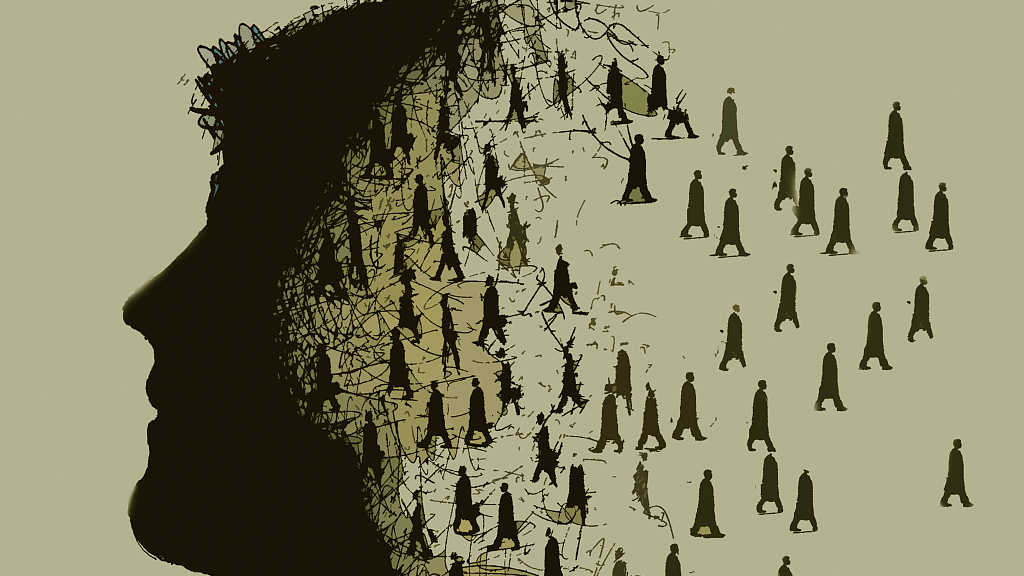 总体来看,贝蒂对“Auslegung”概念的廓清与重塑体现在以下方面:(1)将文本、“富有意义的形式”作为诠释学的中心。精神层面的意义内容具有观念上的客观性,需要借助其客观化物、物理层次的知觉载体来理解,这种载体是心灵的表现形式。诠释学的对象自主性构成客观解释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创作过程是将个体的创造性转换成面向公众的作品,那么理解和解释的过程则是创作过程的倒转,亦即把富有意义的形式“回译”为精神层面的内容。(2)基于诠释学的对象自主性原则,将“解释”和“赋义”区别开来,不能随心所欲地建构文本的意义,要从文本本身出发,通过解释将其固有的客观化内容呈现出来。(3)我们的理解方式规定着我们对对象的理解,在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之后,理解与解释的客观性不可能重新返回到天真的客观主义,解释的客观性最终是一种带有历史性、主体间性,超越并不断拓展个体认知边界的辩证的客观性。“只有当人类精神以客观的意义内容建立一个对立面(Gegenüber),这个对立面如同某种更高的异己之物从生命中生长出来,人类精神才能完成自我认识这一旅程。通过周游于这种意义内容所带来的推动力,我们的精神向自我知识的返回才得以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本体论诠释学的“阐释”概念简单等同于贝蒂所说的“玄想的赋义”。如前所述,海德格尔要求从事情本身出发来修整阐释的前结构,以确保课题的科学性。伽达默尔同样追寻面向事情本身的阐释,尽管“阐释”里面必定包含着“应用”带来的意义多样性、开放性,但并非毫无约束,所探讨的“事情本身”之引导、时间距离的“过滤”都是限制任意阐释的措施。不过,贝蒂认为这些限制措施仍然不能保证解释的正确性。 方法论诠释学对解释的客观性诉求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从个别文本的诠释到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都离不开客观解释作为前提,相应的方法论原则也是必不可少的。客观解释的方法论需要以被解释对象的含义同一性为基础,若没有含义同一性,解释就失去了标准,无法与“赋义”“意义赋予”划清界限。但是,“解释”能否真正通达含义的同一性?伽达默尔在与贝蒂、赫施的争论过程中就提出了质疑:这种同一性是否只是一种抽象的设定。 三、“解释”能否通达含义的同一性 在文本含义的同一性问题上,赫施、贝蒂与伽达默尔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论战双方的分歧主要聚焦于,诠释学能否达到含义的同一性。赫施坚持传统方法论诠释学的“解释”立场:认为伽达默尔的错误在于,混淆了含义(meaning)和意蕴(significance),没有将文本本身的含义和文本在历史关联中的意蕴区别开来;作者在文本中所意指的含义始终是保持同一的(identical),而文本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意义可以发生变化。赫施主张,理解者应当追寻解释的正确性、有效性。“如果他的有效性之要求站得住脚,他就必须使其解释以某个真正的标准为尺度。他所提出的令人信服的唯一规范原则就是那个过时的理想,即正确地理解作者所意指的东西。因此,关于再认识性的解释(re-cognitive interpretation),我的例证并不是立足于强大的道德论据上的,而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它是唯一的解释类型,它有确定的对象,因而它也是唯一能够提出有效性要求的解释类型,无论在那个术语(再认识性的解释——笔者注)的直接意义上还是实际可行的意义上。”赫施将诠释学锁定在认识论、方法论的层面上,解释活动不同于直接的理解,其目的是再认识,因此正确性、有效性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其标准就是含义的同一性、可复制性,无可否认,作者所意指的词义会受到历史变迁的影响而发生意蕴变化,但这正是解释活动需要解决和澄清的问题。“我必须指出,作者意指的词义是确定的、可复制的”,“再认识性的解释探寻作者的意指,这种观点应当成为其他一切解释目标的基石”。 赫施所谓的含义同一性带有很强的实在论色彩,这种同一性是客观的、不可动摇的实在,不依赖于理解主体,在历史中产生的诸多不同的解释可以指向同一种含义。“因此,当我说词义是确定的,我的意思是它是一个自身同一的实体(entity)。而且,我的意思也是说,它是一个从这一刻到下一刻总是保持相同、没有变化的实体。”赫施要求解释必须具有有效性,这一要求植根于含义的同一性,同一文本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会出现不同的解释,产生不同的历史意蕴和效果,而含义的同一性构成了有效解释的尺度,以此为标准来比较、检验各种不同的解释,这是诠释学的规范性要求。 显然,赫施反对伽达默尔关于理解、“Auslegung”和应用互相渗透的观点,重新将三者划界,不仅使同一性的“含义”区别于多元的“意蕴”,后者是在不同诠释学处境中“应用”的“效果”,而且坚持“解释”的认知批判功能,使之区别于“理解”。他认为,理解带有心理、情绪色彩和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因此,这里探讨的真正主题不是如何理解,而是如何评判和批评所理解到的东西。问题在于裁定理解是否可能正确,这最终是有效性的问题”。对于赫施的批评,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再版中指出,理解和“Auslegung”的相互融合,早在施莱尔马赫那里就已得到证明,二者无非是“内在言语”和“有声言语”的关系,这是思想的语言性之必然结果;在其《第3版后记》(1972年)和《古典诠释学和哲学诠释学》(1968年)一文中,伽达默尔进一步表明哲学诠释学的本体论立场,不同于赫施极力凸显解释理论的方法面向和客观性问题,同时表明理解的应用性并不排斥客观性的诉求,“哲学分析揭露出理解具有应用结构,但它绝不意味着限制‘无前提的’准备状态,以便理解文本本身所讲的,它也绝不允许我们把文本‘自己的’意思与文本相脱离,从而使事先想好的观点产生作用”。 贝蒂同赫施类似,主张区分“历史现象的含义/意义(Bedeutung)和它在当今的意蕴(Bedeutsamkeit)”。他批评伽达默尔的理解概念中推出的只是意义变迁,至多是达成一致(Verständigung),漠视了对含义的同一性、客观性要求。“在我看来,伽达默尔提出的诠释学方法,其明显的疑难在于,虽然它为文本与读者之间,即文本表面垂手可得的意义和读者的主观见解之间就事情(Sache)达成一致提供了可能,但并不保证理解的正确性;因为这要求,所获得的理解要完全符合于作为精神客观化物的文本的基础意义。只有这样,结论的客观性才被保证是基于可靠的解释过程。不难证明,他所提出的方法回避了客观性,实际上仅仅涉及有待达成的理解的内在融贯性和确凿性。”伽达默尔的错误在于,混淆了历史解释的诠释学过程与一种受具体境遇所规定的意义赋予,混淆了理解的可能性条件与理解的对象,从而无视诠释学对象作为精神客观化物的自主性,为主观任意的解释开了方便之门。贝蒂对伽达默尔的批评,归根到底在于后者没有区分事实问题(quaestio facti)和法权问题(quaestio iuris),法权问题涉及合法性辩护,而解释“合法性”的尺度在于,符合文本固有的同一性含义。“这问题并不旨在查明在解释中表现出的思想活动里实际发生的东西,而是旨在找出我们应当做什么——即我们在解释任务中应当致力于什么,在正确执行这一任务时使用什么方法以及遵循什么指导原则。”与赫施不同的是,贝蒂弱化了含义同一性的实在论色彩,有意识地克服解释的客观主义,强调解释过程的辩证性和趋向客观解释的无限性。文本的意义必须通过解释才能被重新激活,获得“重生”,并不断发生变化,“但这不排除客观化了的意义内容仍保留他人创造力的客观化这一事实,而解释者不应以任意的方式,而应是借助可控制的指导原则去接近这种意义内容”。贝蒂设定文本的同一性含义是一种稳定客观的存在,在解释过程中会衍生出变化的意蕴,那种含义同一性作为理想,需要解释者以不断“接近”的方式来实现。 尽管伽达默尔提出,时间距离具有过滤作用,能够区分真假前见,但这并不能使贝蒂满意,这种区分不能避免客观性失落的结果,无法为理解的正确性提供一种可靠的标准。同样,贝蒂的诠释学方案也没有完全说服伽达默尔,“E.贝蒂试图通过机智的辩证法在主观和客观的共同作用中证明浪漫主义诠释学遗产的合理性,然而,自从《存在与时间》指出主体概念具有本体论上的前把握性,以及后期海德格尔在‘转向’(Kehr)思想中冲破了先验哲学反思的范围之后,甚至这种机智的辩证法也必然不能令人满意”。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第2版序言中声明,他并不否认贝蒂在诠释学方法论方面所做的卓越工作,但方法论问题不是其探究的根本目的,他要证明的是理解的真实运作过程如何,亦即效果历史运动。 况且,在伽达默尔看来,追求抽象的含义同一性仍然是一种客观主义,“倘若从超立场的立场出发去思考问题的真正同一性,这种超立场的立场乃是一个纯粹的幻觉”。不存在这样一种抽象的同一性,理解总是不同地去理解,它“决不可能固定于一种僵死的同一性之中”。贝蒂固然已提出“辩证的同一性”(dialektische Identität),但伽达默尔认为,这种同一性并没有真正摆脱心理主义和实在论的色彩,因为贝蒂仍然要求理解者借助于心理工具实现作者创作过程的倒转。贝蒂宣称,“解释者应当以这样一种方式把他自己生动的现实性带入与他从对象所接受的刺激紧密和谐一致之中,以致我们和他人以一种和谐一致的方式进行共鸣”。他一方面要求避免主观意见达到正确的理解,“另一方面仍然如此紧密地跟随着施莱尔马赫所创立的‘心理学解释’,以至于他的诠释学立场总是面临再度模糊的危险。他如此努力地克服心理学的狭隘,并将重构价值和意义内容之间的精神联系视为任务,却也只能够通过一种类似心理学解释的方式才能为所提出的这种真正的诠释学任务进行奠基”。 通过与贝蒂、赫施的论争,伽达默尔在含义的同一性问题上做出一定调整,亦即不放弃对同一性的追寻,同时力图调和同一性和多元化的对立,使作品的同一性和阐释的开放性、多样性协调起来。“再认识即理解的同一性的起点是作品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还决定着同一性是与变化和差别紧密相联的。任何作品几乎为每一个接受它的人让出了一个他必须填充的游戏空间。”这里我们注意到,伽达默尔把含义的同一性替换成了作品的同一性,其中填充了意义的变迁流转,但他仍然没有解决,多元意义的阐发之合理性、正确性边界在哪里,也没有提供切实可操作的方法规则。伽达默尔在很大程度上绕开了解释的客观性问题,直接切入本体论层面。 公允地看,当代方法论诠释学在廓清重塑解释概念、捍卫解释的客观有效性、丰富发展诠释学方法论方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在含义的同一性上,方法论诠释学未必一定会陷入抽象的客观主义,特别是贝蒂提出的辩证同一性概念,使文本、作者和解释者三大要素协同运作,为解释的客观性提供了可能。我们认为,诠释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维度不可或缺,正确解释的问题不可回避,即使在伽达默尔本人的哲学诠释中,也仍然包含着方法论的要素(现象学、辩证法),“以为方法论诠释学是被本体论诠释学所超越、扬弃了的、没有生命力的旧有传统,因而只具有思想史的价值,才是对诠释学的真正误解”。 余论:“Auslegung”的汉译问题 基于以上考察,最后我们对“Auslegung”的汉语译名略作探讨。根据不同的翻译标准,有两种基本方案:(1)按照概念的内涵翻译,在追求客观义的方法论诠释学那里,将“Auslegung”译为“解释”,而在主张延伸义的本体论诠释学那里则译为“阐释”;若原文交替使用“Auslegung”和“Interpretation”,不作明确区分,则按其内涵将二者都译为“解释”或“阐释”。这一方案的优势在于,能够准确译出术语的涵义,缺点是“一词多译”和“多词一译”,妨碍了译入语读者对原文信息的判断。(2)按照一一对应的标准,将“Auslegung”译为“解释”,将“Interpretation”译为“阐释”,或者反过来,将“Auslegung”译为“阐释”,将“Interpretation”译为“解释”。这一方案的优势在于“一词一译”,缺点在于不能准确反映这一概念在不同诠释学流派中的内涵及其流变。此外,还存在一些特殊的难点,例如,在狄尔泰那里,“Auslegung”和“Interpretation”为同义概念,但其内涵具有过渡性和双重性,兼有“解释”和“阐释”之义;海德格尔时而不区分“Auslegung”和“Interpretation”,时而又区别对待。 综上,如果按照概念内涵翻译,并且在关键之处标注相应的原文或增加注释予以说明,那么,既能准确传达概念的涵义,又能方便读者辨识术语的原貌。这种做法有利于学术研究,但在原著翻译中却难免有“越俎代庖”之嫌,即译者将自己对原文的理解直接输入给读者,代替了读者自己的思考。不过,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翻译本身就已经是阐释,译者确实不可能抛弃自己的理解来从事翻译。 如果按照一一对应的标准,我们更倾向于将“Auslegung”译为“解释”,将“Interpretation”译为“阐释”或“诠释”。“诠释”在汉语中并不局限于考据原义,也不局限于普通读者对神圣文本、经典文本的“仰视”性阅读,它完全可以表达对意义的创造性延展。鉴于“诠释”含义的丰富性、广泛性,可以囊括不同流派的旨趣,笔者认为,以“诠释学”翻译“Hermeneutik”更为恰当。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诠释学与人文科学的逻辑”(2021BZX002)的阶段性成果〕
|